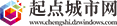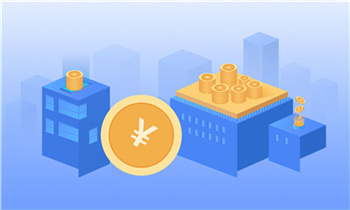读有关老北京的书籍,经常会提到豆汁儿这个饮品,有人趋之若鹜,每天要喝上一碗过把瘾。梁实秋先生是正宗的老北京,他在《豆汁儿》一文中写道:“自从离开北平,想念豆汁儿不能自已。”但似乎除了正宗老北京人之外,外地人都无法接受或喜欢豆汁儿,就算捏住鼻子下咽,甚至还会恶心再吐出来。
在我之前的想象之中,豆汁儿也许就是很臭很臭的臭豆腐卤,还有点酸,这个臭的程度,无法想象。
 (相关资料图)
(相关资料图)
我曾经有长达数年的时间,每月要去北京开月度销售会议,但是,从来都没有机会品尝过豆汁儿,也许北京的朋友们认定我们这些非北京土著根本是不可能会喝下去这个豆汁儿的。7月中旬,我应邀去北京,想着好多朋友多年未见,就微信约卞爷、逸良、庄子等好友小聚。卞爷曾经在上海记者站工作二十多年,对于来自上海的朋友就特别热情,他执意要请客,并安排在“满福楼”吃涮羊肉。
满福楼老板就姓满,回民,是卞爷的好朋友。店堂的装饰也完全是老北京风格。席间聊到了豆汁儿,我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于是,卞爷马上安排服务员上了豆汁儿,这也是我的第一次。
豆汁儿上桌之后,邻座祖籍北京的庄子小姐也认定我是无法喝下这豆汁儿的。我勺了一小碗,用鼻子凑近闻了闻,是有点臭味,但感觉似乎并没有想象的那么臭,也就增强了喝下这碗豆汁儿的勇气。于是,我主动挑战庄子:“我喝这一小碗豆汁儿,你喝一大杯葡萄酒,如何?”庄子小姐不仅接受这个挑战,还特别容许我可以捏着鼻子喝。想不到我端起小碗,把豆汁儿一饮而尽。其实我已经想好了,快速喝光并吞下,这是个策略,也就不至于喝到一半难以下咽而进退两难。此时的庄子也只能端起酒杯,把我带去的乐吉隆干白葡萄酒一口闷掉。
在座的北京朋友自然佩服我的勇气,我这才开始细细回味豆汁儿的滋味,豆汁确实有点臭,有点馊腐的味道,但也不至于难以下咽。我是非常喜欢吃江南的臭豆腐,近年来,也是很少吃到很臭的臭豆腐,如果不是很臭,吃到嘴里,这个臭豆腐就不会很香。也许正是多年来吃臭豆腐的功底,让我可以大胆喝下这碗豆汁儿。
接着请教卞爷,才明白了豆汁儿其实和大豆没有关系,是用制作绿豆粉丝的残余物,经发酵产生的豆汁,具有养胃、解毒、清火的功效。根据文字记载,豆汁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在乾隆时期,豆汁儿已经成为宫廷饮料了。
老北京是不讲豆汁的,加了一个儿字,叫豆汁儿。于是,我把上面写的豆汁全部改成了豆汁儿。
喝豆汁儿,店家还配了一小碟大头菜。如果客人喝了豆汁儿而醋心,说是吃一点酱菜,就过去了。
曾经读过谢蔚明先生的文章《豆汁儿》,他说京剧名家言慧珠就特别爱吃豆汁儿,所以,唱起来也是特别有韵味。老友们都知道,酒足饭饱之际,卞爷也会开唱京剧选段,一声“沙奶奶,您听我说!”十足的老北京腔,好像还真有点豆汁儿的味道。
北京孟春明先生也曾经在文章中写道:“检验一个人是不是地道北京人的最简便的方法之一,莫过于请他喝豆汁儿。”我祖籍是河北深州,生长在上海,虽然第一次吃豆汁儿和麻豆腐,却并没有违和感,难道是基因在发挥作用?以后有机会,我还要再试试。也许,我也会像梁实秋先生一样,想念豆汁儿不能自已。(刘国斌)